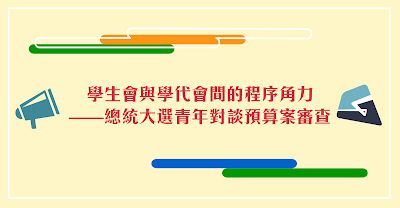◎傅彥龍
數日的田野訪調,我們聽聞部落工作者的默默耕耘,以及他們對未來方向的尋索。不過看似激勵人心的部落營造,實則不斷面臨部落外國家與社會結構作用而生的困境,以及部落內部外來資源的分配與對外代表性的爭端。這些複雜難解的局面,隱隱然指向歷史脈絡中的源頭:自漢人開發的足跡到來,以及日本、中華民國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其國家的統治力量將觸角伸入自給自足、與世無爭的港口部落,便打破幾千年來的平衡,預示了自彼以後無休止的紛擾。
資源進駐惹的禍
1990年代開始,原住民族運動在正名與自治等政治運動後,出現一波「部落主義(tribalism)」的新運動路線,強調回到部落以草根力量重建傳統文化。伴隨著1994年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以及1996年原民會成立後對社區營造與傳統文化活動的資源挹注,開啟了部落營造的風潮,例如成立社區組織、發行刊物、恢復失傳的祭典、記錄並保存傳統文化等(阮俊達, 2015)。港口部落的文化復振工作也是此一風潮下的一例。
國家的補助政策某種程度上雖是文化復振的助力,卻也往往在許多部落裡產生問題。為了取得資源,部落工作者必須了解如何與官僚體制打交道,資訊的取得、複雜的報告撰寫、到會計核銷等行政作業,無形中設下了排除性的門檻,只有華語能力好、熟悉漢人社會和國家官僚體制思維的人才可能勝任(阮俊達 2015)。此外,公部門僵化的補助類別,使得活動與硬體設備以外的軟體與長期培力被忽略,計畫結束後無法留下永續的能量(阮俊達, 2015)。此外,長期寫計畫爭取資源的部落工作者,若沒有注意將資源適度分配,就可能違反部落的傳統分配倫理,引來其他族人的誤解。然而錯誤其實不全在工作者本身的疏失或是族人不同的想法,如同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教授謝若蘭所言:「是這整套體制教他們用這種遊戲規則去處理。」
基於前車之鑑,在東華大學「新世紀東臺灣的脈動─經濟生活、人文創新與社會培力」計畫中,謝若蘭帶領的港口團隊有過深刻的討論:過去許多學者對原住民族的研究「都是踩著部落的經驗,獲得自己的研究成果,但是很少能夠在沒有任何研究的成果之下好好地參與部落事務」。因此,他們最後的共識是:來到部落中,不做研究也不帶入資源,也要避免最後只成就了某一方的利益,只做共同參與學習。經過與各方的討論形塑出的「最大公約數」就是民族教育 [註1]。後來港口社區發展協會、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東華大學「東台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中心」、港口國小、藝文職人工作室等六個單位更為此簽了一項合作備忘錄。然而,備忘錄的意義並不僅止於促進合作,它背後牽涉到原住民族集體歷史中的「殖民創傷」。
殖民陰影與失落的同意權
對於台灣原住民族而言,「簽約」是個敏感的字眼。近代以來,原住民族在與荷蘭、西班牙、清國、日本、中華民國等外來政權交手的過程中,由於外來的契約概念與原住民族傳統價值的差異,以及語言的不熟悉,原住民族往往因此受騙,契約成為被外來者恣意詮釋、用以合理化自身掠奪行為的不平等條約。「簽約」後,部落賴以為生的土地等自然資源以及重要的文物因此被奪走,形同「整個部落被賣掉」。
2005年原住民族基本法公布實施,其第二十一條規定任何人從事影響部落權益的作為,需要取得部落的集體同意 [註2],然而,法條指的「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未明確指出到底誰能同意?是身為傳統領袖的頭目?身為地方行政首長的村長?還是部落發展協會?這樣原則性的法條至今缺乏細則做更詳盡的規範。此外,面對各部落的多元歧異,現代法律往往無法一體適用所有部落,而法律中以西方理性思維為基礎的個人權利觀,和原住民族傳統文化強調的社群權利觀更是有所扞格(阮俊達, 2015)。
備忘錄:重拾權利的嘗試
合作備忘錄是一個改變的嘗試。部落大學校長Sifo表示,一方面為了推動民族教育,另一方面為了實踐原基法第21條的在地集體同意權,他和各團隊合作催生這個以阿美族語和華語並列的合作備忘錄,以阿美語書寫強調港口部落在當中的主體性;當中提到六方將協力進行部落知識建構與傳承教育,共享合作機制中產出的文史、藝術、海岸知識。合作實施方式也規定相關計畫由六方或雙方人員共同協商,有必要時可以制定細節或但書。這項契約有效期一年,期滿經協商同意後得以延長,或是在期滿前通知對方終止協定。
在過去,有些學術團隊只要其計畫通過研究倫理審查(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就擅自進入部落。這些審查一般缺乏部落在地人的參與,遑論原基法21條規定的部落集體同意權。因此,Sifo希望備忘錄能夠拋磚引玉,以港口部落做為起始典範,規範學術單位在部落做任何事情都必須另外與部落簽約,取得部落的同意。倘若成功,未來能夠讓其他部落一起來推行。謝若蘭也指出,備忘錄的意義在於形塑合作的基礎,是宣示性的自律公約。
不過,合作備忘錄的簽訂並非毫無爭議,其中一個爭議便是代表性的問題。有人質疑:「港口發展協會憑什麼代表部落來簽訂此一備忘錄?」尤其在面臨現代國家體制的統治與主流社會的互動時,許多原住民族部落更是經常面臨「誰能代表部落?」的問題。Sifo認為,代表性的機制只能透過部落內部的討論與協商,由部落自身共同建立一套整體對內對外的一致窗口,而他身為外人無權置喙。
但是,Sifo認為原住民族置身在目前受中華民國殖民的困境下,主動建立一套以部落為主體,國家或部落以外的單位為客體的互動機制是重要的。他指出,簽約雖在歷史中多為負面的,但國際上也有正向的前例。以紐西蘭毛利人與英國簽訂的《懷唐伊條約》(Treaty of Waitangi)為例,毛利人在1970年代的抗爭,對該條約的翻譯提出異議,並且重新強調該條約的重要性,依此要求紐西蘭政府履行條約,針對過去主流社會的不平等對待與傳統領域的剝奪,給予補救與賠償,繼而迫使紐西蘭政府在1975年成立懷唐伊調解庭(Waitangi Tribunal),毛利人因此得以藉此取回傳統領域,並以所得的賠償建立一套毛利人的教育與醫療體系。Sifo談到,台灣原住民族未來或許可以嘗試參考毛利人的模式,以港口部落為起點逐步實踐部落與外界的簽約,並且推廣到其他部落,一旦累積形成一股力量,就可能施壓要求政府與原住民族簽約,藉此取回原住民族應有的一切。
這是一種尋求原住民族出路、解除殖民的積極策略,然而我們也要反思,建立部落整體的代表機制和簽約的作為,是否仍舊被迫臣服於主流社會訂下的遊戲規則。現代國家體制對於部落的治理,產生出單一對口的需求,而契約同樣來自於主流社會,其簽訂需要熟悉國家法律語言邏輯,如此是否可能在推動過程中面臨其它問題?接受主流社會的遊戲規則,是否等同先行承認了長期邊緣化原住民族的主流社會價值具有較高正當性?簽訂契約時,華語與族語邏輯的歧異是否導致誤解,並且扭曲了權利的內涵,使部落蒙受損失? [註3]但是,原住民族處在當前的情況下,若不藉由簽約的途徑,是否還有其它的可能?這些問題儘管經過前人的反覆辯證,仍需要在未來持續嘗試與摸索。
結語
台灣原住民族遭受上百年的外來殖民,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各層面受到剝削與邊緣化,許多族人失去自我的民族認同。在歷史上的此刻,部落面臨當代國家統治與資本主義經濟帶來的泥淖,最初的「原」鄉是否已然難以辨識?不同的部落或許只能靠自己從現有的社會脈絡中摸索各自的出路。回望港口部落,在不同議題上——土地與產業發展、藝術能量的整合、教育轉型的發展、文化紮根與認同等——各有其自身龐雜的發展脈絡,以及人們認知上的歧見。如同地方文史工作者Lafay所說的:「如何從已然分工的狀態中產生共同的需求與相互連結,將有待時間來磨合。」
--------------------------------------------------------
註解
[1] 民族教育的討論可參考本刊文章〈港口部落教育何去何從〉。
[2]《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前半部規定:「政府或私人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生態保育及學術研究,應諮商並取得原住民族或部落同意或參與,原住民得分享相關利益。」
[3] 這樣的問題與原運中自治與獨立路線的分歧有相似之處,阮俊達(2015)在〈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軌跡變遷(1983-2014)〉第89頁提及陳舜玲(2002)的分析指出:「原運雖以去殖民觀點挑戰國家統治正當性,卻又難以拒絕國家權力在各種生活層面的作用,只好尋求進入體制落實權利主張…是否等同先行承認國家統治的正當性?另一方面,要在既有法秩序下主張原住民族權利,需要先熟習國家法律與政治制度的邏輯,結果經常遭遇法律語言轉換上的困難、更無法保證在政治過程中能達到原先設定的目標。」
參考資料
1.阮俊達,2015,〈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軌跡變遷(1983-2014)〉,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碩士論文。
2.Treaty of Waitangi. (2015, September 17).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Retrieved 12:59, September 28, 2015, from https://goo.gl/bxUUEW